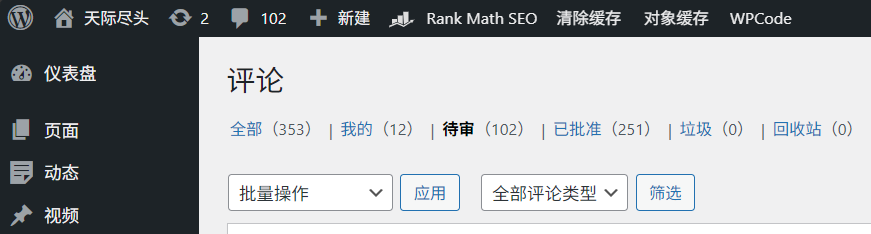他为什么不结婚

夜色落在城市的边缘,把街角切成了两种截然不同的温度。
昏暗处,一个年轻人正收拾散落在地上的文件:绩效考核表、房租合同、信用卡账单……纸面在冷光里泛出些许锋利的白。他脚边散落着外卖保温袋,一辆共享单车倒在一旁,高房价广告牌被风掀起一角,像某种被撕碎又丢弃的承诺。
另一侧却仿佛是另一个世界。暖光从商圈的玻璃幕墙泼下来,把那片区域照得明亮柔润。一个穿着红色西装的老板站在那里,金表在灯下闪着短促的反光。他一只手举着咖啡杯,语气轻松,像刚从一场成功的交易里赚了一大笔。身边两位女子各自散发着不同的光泽,她们的表情不尽相同,却都带着一种从高处俯视世界的轻盈。
三人站在温暖明亮的光里,像站在舞台的中央。光与影在地面划出一条分界,清楚得像线条。
他们望向街角的年轻人,彼此交换着几句不紧不慢的评论:“他为什么不结婚”,语气里带着不解与某种莫名的期待。